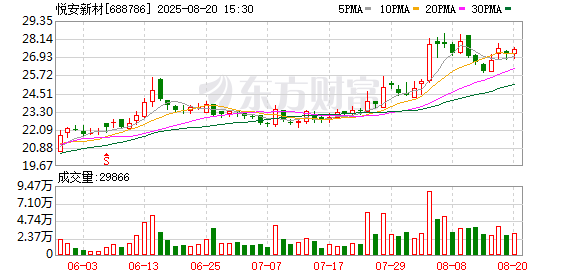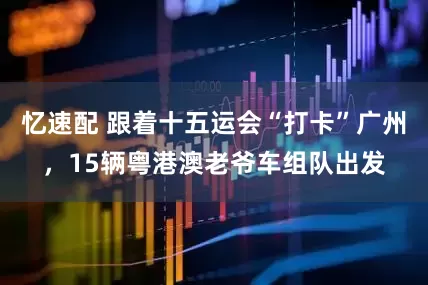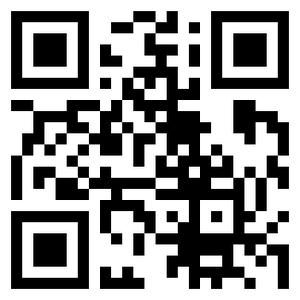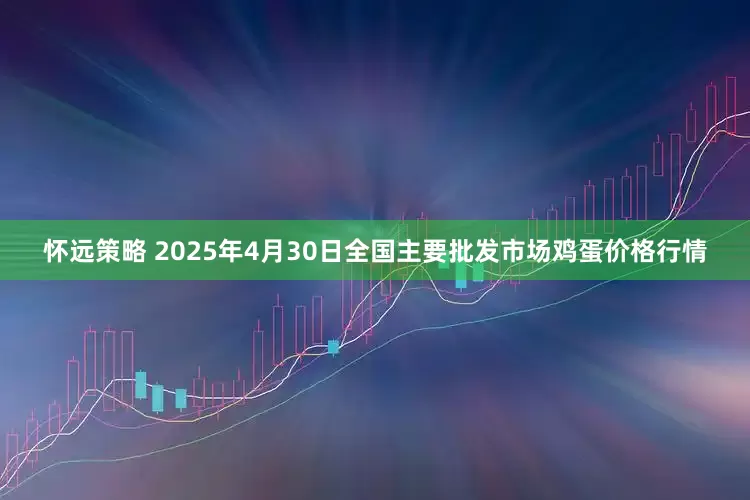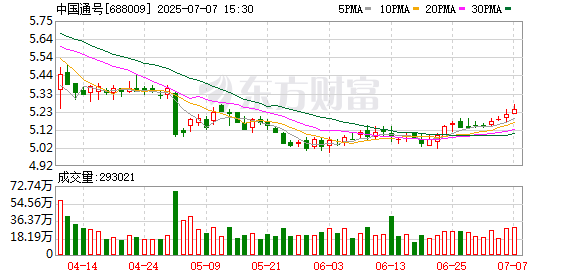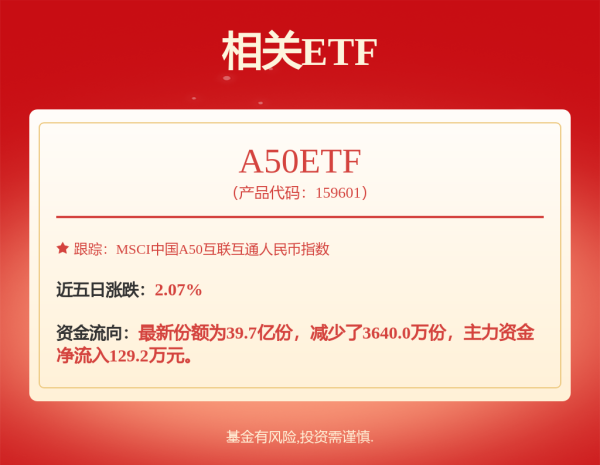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趣策略
讲述人/赵小兰 撰写/情浓酒浓
(声明:作者@情浓酒浓在头条用第一人称写故事,非纪实,部分情节虚构处理,请理性阅读)
我叫赵小兰,出生在陕南农村。我们村子坐落在秦岭脚下,不大不小,一百多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。那时候的农村日子过得清贫,孩子们却总能找到乐子。
1986年的夏天,我八岁,弟弟赵小勇才三岁。
记得那天傍晚,我正在院子里帮娘剥包谷粒,弟弟蹲在门槛上玩石子。村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:“今晚七点半,村部放映电影《少林寺》,欢迎社员同志们前来观看!”
弟弟一听就蹦了起来,像只小兔子似的窜到我身边:“姐!姐!放电影!我要去看!”
娘抬头看了眼天色:“你爹今儿个又不在家,铁路上忙,娘还得剥这些玉米……”
展开剩余87%“娘,我带弟弟去!”我赶紧说,“我都八岁了,能看好弟弟。”
娘犹豫了一下,终于点点头:“那你们早点去占位置,看完电影赶紧回来,别在路上贪玩。”
我高兴地应了一声,拉着弟弟就去屋里搬那条我们家常坐的长条凳。凳子是用老槐木做的,沉得很,但我和弟弟都习惯了,一人抬一头,晃晃悠悠地往村部走。
从生产队到村部有六七里地,要穿过一片苞米地和几道田埂。夕阳西下,金色的余晖洒在绿油油的庄稼上,远处的秦岭像一道青黑色的屏风。弟弟一路上蹦蹦跳跳,嘴里不停地问:“姐,少林寺是不是有和尚打架?是不是像孙悟空那样厉害?”
“听说可厉害了,一个能打十个呢!”我逗他。
“那我长大了也要当和尚!”弟弟挥舞着小拳头,差点把凳子摔了。
我们到村部时,晒谷场上已经支起了白色的幕布,不少孩子围着幕布转圈玩耍。场边几个小贩支起摊子,有卖冰棍的、卖瓜子的,还有个推着自行车卖糖葫芦的。
弟弟一看到那红艳艳的糖葫芦就走不动道了,拽着我的衣角:“姐,我要吃那个……”
我摸摸口袋,里面有娘给的五分钱:“只能买一个啊,咱俩分着吃。”
卖糖葫芦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,皮肤黝黑,眼睛却亮得吓人。他见我们过来,立刻堆起笑脸:“小妹妹,给弟弟买糖葫芦啊?又甜又脆,五分钱一串!”
我掏出钱,他却不急着接,反而蹲下身逗弟弟:“小弟弟几岁啦?叫什么名字呀?”
弟弟怯生生地躲在我身后,又忍不住偷看那些糖葫芦:“我叫赵小勇趣策略,三岁了……”
“哎哟,真乖!”那人摸了摸弟弟的头,又抬头问我,“你们爹娘怎么没跟着来啊?”
“爹在铁路上班,娘在家干活。”我老实地回答,心里却觉得这人问得有点多。
那人听了,眼睛眯成一条缝:“真是懂事的姐姐。”说着,他取下两串糖葫芦递给我们,“来,多给你一串,弟弟这么可爱。”
我接过糖葫芦,总觉得他看弟弟的眼神怪怪的,像是我们家大黄狗看见肉骨头的眼神。但我没多想,谢过他就拉着弟弟去找位置了。
晒谷场上人越来越多,我们找了个靠前的位置放下凳子。弟弟坐在我腿上,小口小口地舔着糖葫芦,眼睛亮晶晶的。天渐渐黑了,放映员开始倒胶片,一束光打在幕布上,全场孩子都欢呼起来。
电影里的打戏特别精彩,看到醉棍对打时,弟弟激动得站在凳子上学动作,差点摔下来。
电影放完时已经十点多了。晒谷场上乱哄哄的,大人们喊着自家孩子的名字,大家拎着凳子匆匆往家赶。我一手扛着长条凳,一手牵着弟弟,跟着人群往外走。
出了村部,人群渐渐分散。我们生产队的人不多,走到半路,就只剩下前面几个模糊的背影了。月光特别明亮,照得土路明晃晃的。
弟弟走了一会儿就开始闹:“姐,我走不动了……脚疼……”
我蹲下身看他,小家伙眼睛红红的,确实累了。我只好把凳子夹在腋下,背起他:“那你趴好了,别乱动。”
弟弟软软的身子贴在我背上,很快就睡着了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,渐渐跟不上前面的人了。月光下的田野静悄悄的,只有蛐蛐在叫。路两旁的苞米长得比人还高,黑黢黢的像两堵墙。
突然,我听到身后苞米地里传来“沙沙”声,像是有人在里面走动。我猛地回头,却什么也没看见。
“大概是野兔子吧。”我安慰自己,加快脚步往前走。
刚走几步,那“沙沙”声又来了,这次更近、更清晰。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,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我不敢回头,但月光把影子投在前面的路上——我的影子后面,还有一个长长的影子,头上好像有很多触角一样的东西!
“啊!”我尖叫一声,丢下凳子,背着弟弟就跑。弟弟被惊醒,吓得哭起来:“姐!姐!怎么了?”
我顾不上回答,拼命往前跑。可是那“沙沙”声像是粘在身后似的,我跑多快它就跟多快。弟弟在我背上哭得更大声了,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。
“扑通”一声,我被什么绊了一下,重重摔在地上。弟弟从我背上滚下来,哭得更凶了。我顾不得疼,赶紧爬过去抱住他。身后的“沙沙”声突然停了,四周静得可怕。
我浑身发抖,紧紧搂着弟弟,一动不敢动。月光照在我们身上,我能听见自己“咚咚”的心跳声。
就在这时,一只大手突然拍在我肩膀上!
“啊!”我又是一声尖叫,差点把弟弟扔出去。
“吃……”一个含糊不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我战战兢兢地抬头,看见一根烤得焦黄的玉米递到面前。
借着月光,我认出了那张熟悉的脸——是我们村的守村人杜有为。他四十多岁,因为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,说话不太利索,村里人都叫他“杜傻子”。他住在村口的破庙里里,平时帮生产队看看庄稼,谁家有事也去帮忙。
“杜……杜叔……”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。
杜有为蹲下身,笨拙地拍了拍我的头:“回家。”他说话总是很简单。
我抹了把眼泪,背起还在抽泣的弟弟。杜有为捡起我丢下的长条凳,跟在我们后面。有了他在,我的心总算踏实了些。
走到能看到我家灯火的地方,杜有为把凳子还给我,指了指家的方向:“回家。”然后转身要走。
“杜叔,谢谢你……”我冲他背影喊了一句。他摆摆手,没回头,身影慢慢消失在月色中。
娘听到动静迎出来,看见我们狼狈的样子吓了一跳:“这是咋了?摔着了?”
我摇摇头没多说,怕吓着娘。那晚我做了整夜的噩梦,梦里总有一个头上长满触角的黑影在追我们。
第二天一早,村里就传开了消息:昨晚那个卖糖葫芦的是个人贩子,专门拐小孩的!他在隔壁村想抱走一个孩子时被发现了,村民们追打他,让他跑了。
我听到这消息,浑身冰凉——那个黑影头上的“触角”,不就是插糖葫芦的草把子吗?他一定是盯上了弟弟,一路跟着我们……
后来爹回家听说了这事,特意买了半斤水果糖让我给杜有为送去。我去破庙找他时,他正蹲在门口啃生红薯。见我来了,他咧嘴一笑。
“杜叔,谢谢你那天晚上……”我把糖递给他,突然发现他的右手腕上有一道新鲜的伤痕,像是被什么尖锐物体划的。
他接过糖,剥开一颗塞进嘴里,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:“甜。”然后像是想起什么似的,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木雕递给我——是一只粗糙但可爱的小鸟。
“给……弟弟……”他结结巴巴地说。
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这个被村里人叫了一辈子“傻子”的人,却有着最纯净的心灵。
如今我早已离开村子,在城里安了家。 去年回乡,听说杜有为已经去世了。村里人说,他走得很安详,是在睡梦中离世的。我去他坟前烧了纸,放了一串糖葫芦。
下山时,我遇到了当年的村支书,现在已经白发苍苍。他告诉我一个秘密:那年人贩子事件后,他们在苞米地里发现了一把刀和几滴血迹。原来那晚杜有为不只是碰巧路过,他是听到我们的尖叫声,不顾危险冲进苞米地和人贩子搏斗,才救下了我们。
我站在山路上,望着远处已经变了模样的村子,泪水模糊了视线。那个夏夜的恐惧早已淡去,但杜有为带给我们的温暖,却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,像一盏不灭的灯。
如今弟弟也有了孩子趣策略,我常给他讲那个关于糖葫芦、月光和守村人的故事。故事的最后,我总是说:“这世上有些人看起来不太聪明,但他们心里装的,是最珍贵的善良。”
发布于:山西省米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